
HASHKFK
OD体育官方网站(OD SPORTS)全球赔率最高在线投注平台(访问: hash.cyou 领取999USDT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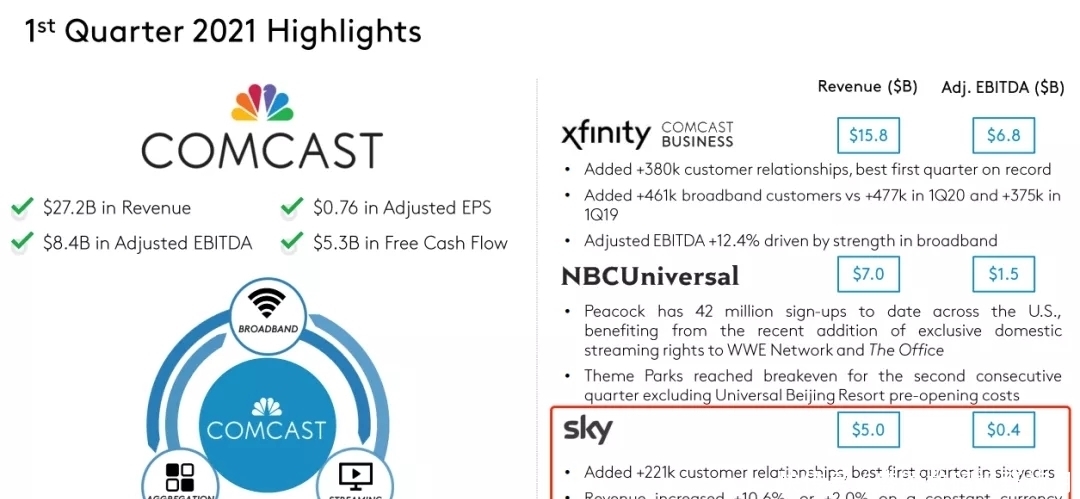
在《新学伪经考》一书中,康有为将古文经学尤其是《左传》斥责为伪经,认为它们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。康有为这么做,目的是否定传统流传的儒家经典的权威,将当前的中国文化说成并非儒学真正的东西。这样一来,否定当前文化并对中国制度进行改革,不但不是反对儒学,反而有利于它的重新发现。在《孔子改制考》一书中,康有为之所以将孔子说成是改革者,目的是用当时人普遍信奉的儒学信仰为制度改革寻找依据,并达到这样的目的,即所有给人以印象深刻的西方价值都曾经“是中国的东西”。在《大同书》中,康有为把孔子描述成儒家乌托邦的进化预言家,认为中国跟西方一样,都走在通向未来大同世界的进化道路上。所以,在康有为这位提倡引进西方制度甚至文化的人眼里,儒家血统与西方精神是一致的,现在的任务是恢复这一血统,并借此与西方一起进化到未来的乌托邦,即儒家今文经《公羊传》所构想的“太平世”:“在太平世里,实现了自由、平等,没有人与人的不同和同与同的区分。
在上述背景下,到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从接受西方器物、制度到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的行动,兴起了新文化运动。在这场运动中,又先后或大致同时出现了两种略有区别的思潮:一种认为接受西方文化是“择东西之精华而取之”的过程;另一种则认为接受西方文化是“服从真理”而必须的过程。“择东西之精华而取之”思潮的产生,源自中国思想家面对以下两种无法调和的冲突:作为中国人,“他既应对中国的过去怀有特殊的同情,但同时又必须以一种客观的批判态度反省中国的过去。能满足这两项要求的最合适的方法,就是将西方和中国所能提供的精华结合起来”。鲁迅先生提出的取其精华、弃其糟粕的“拿来主义”,就是这种思潮的最好表达。显然,此处的“精华”一词,在文化上是一个中性术语,它在社会心理上有助于中国人大力吸收西方的文化,同时也不否认传统中可能有值得保留的好东西,“符合现代人各自的标准的价值”。由此可见,判断是否精华以及什么才是吸取精华的恰当方式,其标准是唯一的,那就是现代的价值或者说是真理。
第一个原因来自太平天国以来的社会反抗运动的需要。中国传统社会掀起的反抗运动,其思想资源基本来自佛教(如白莲教徒多次发动起义)或道教(如太平教义指导下的黄巾军起义),它们期望推翻目前的政治经济统治集团,建立更加公道的社会。但这样的思想资源,本身指导性极为有限,到20世纪初在中国根本没有什么影响。本来富有潜力的基督教,在中国也没有得到大的发展,而且作为一种社会抗议的象征符号,基督教并不具有激进的物质进步的许诺。儒教由于跟统治集团紧密联系在一起,因此坚决否认社会抗议的必要。在当时正处于日益加深的政治经济危机中的中国,社会底层迫切要求有这么一种思想:它既能用作指导思想,以反抗应为危机负责的统治集团,又能带来基督教所无法提供的物质进步,以克服深重的危机。于是,众多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,相信就是这样一种指导思想,它既能为反抗统治集团提供指导,也能带来物质的进步以克服时代的危机。